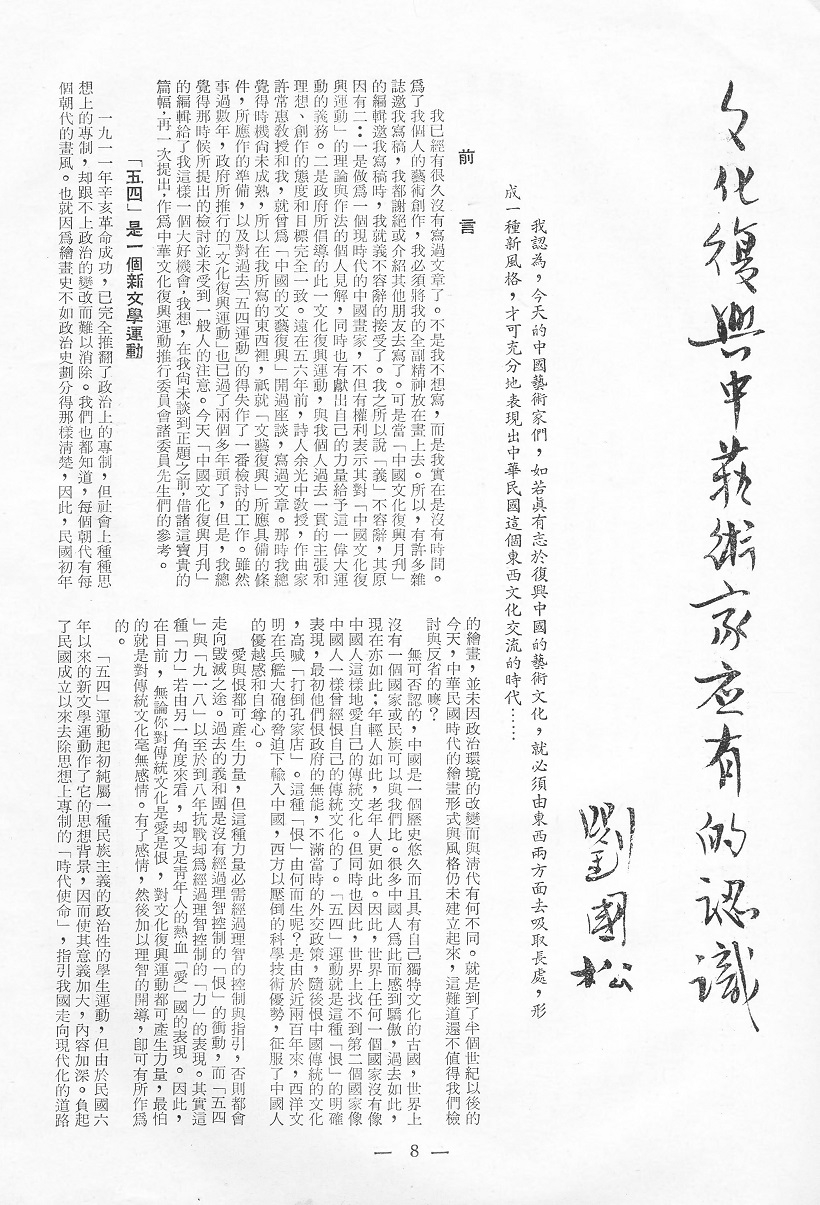文化復興中藝術家應有的認識
- 期刊與書籍
- 《中華文化復興月刊》第17期
- 8至11頁
- 1969.8
- 劉國松
我認為,今天的中國藝術家們,如若真有志於復興中國的藝術文化,就必須由東西兩方面去吸取長處,形成一種新風格,才可充分地表現出中華民國這個東西文化交流的時代……
前言
我已經有很久沒有寫過文章了。不是我不想寫,而是我實在沒有時間。為了我個人的藝術創作,我必須將我的全副精神放在畫上去。所以,有許多雜誌邀我寫稿,我都謝絕或介紹其他朋友去寫了。可是當「中國文化復興月刊」的編輯邀我寫稿時,我就義不容辭的接受了。我之所以說「義」不容辭,其原因有二:一是做爲一個現代的中國畫家,不但有權利表示其對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」的理論與作法的個人見解,同時也有獻出自己的力量給予這一偉大運動的義務。二是政府所倡導的此一文化復興運動,與我個人過去一貫的主張和理想、創作的態度和目標完全一致。遠在五六年前,詩人余光中敎授,作曲家許常惠敎授和我,就曾爲「中國的文藝復興」開過座談,寫過文章。那時我總覺得時機尙未成熟,所以在我所寫的東西裡,只就「文藝復興」所應具備的條件,所應作的準備,以及對過去「五四運動」的得失作了一番檢討的工作。雖然事過數年,政府所推行的「文化復興運動」也已濄了兩個多年頭了,但是,我總覺得那時候所提出的檢討並未受到一般人的注意。今天「中國文化復興月刊」的編輯給了我這様一個大好機會,我想,在我尙未談到正題之前,借諸這寶貴的篇幅,再一次提出,作爲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諸委員先生們的參考。
「五四」是一個新文學運動
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成功,已完全推翻政治上的專制,但社會上種種思想上的專制,却跟不上政治的變改而難以消除。我們也都知道,每個朝代有每個朝代的畫風。也就因爲繪畫史不如政治史劃分得那樣淸楚,因此,民國初年的繪畫,並未因政治環境的改變而與清代有何不同。就是到了半個世紀以後的今天,中華民國時代的繪畫形式與風格仍未建立起來,這難道還不值得我們檢討與反省的麼?
無可否認的,中國是一個歷史悠久而且具有自己獨特文化的古國,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或民族可以與我們比。很多中國人爲此而感到驕傲,過去如此,現在亦如此;年輕人如此,老年人更如此。因此,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沒有像中國人這樣地愛自己的傳統文化。但同時也因此,世界上找不到第二個國家像中國人一様曾經恨自己的傳統文化的了。「五四」運動就是這種「恨」的明確表現,最初他們恨政府的無能,不滿當時的外交政策,隨後恨中國傳統的文化,高喊「打倒孔家店」。這種「恨」由何而生呢?是由於近兩百年來,西洋文明在兵艦大砲的脅迫下輸入中國,西方以壓倒的科學技術優勢,征服了中國人的優越感和自尊心。
愛與恨都可產生力量,但這種力量必需經過理智的控制與指引,否則都會走向毁滅之途。過去的義和團是沒有經過理智控制的「恨」的衝動,而「五四」與「九一八」以至於到八年抗戰却爲經過理智控制的「力」的表現。其實這種「力」若由另一角度來看,却又是靑年人的熱血「愛」國的表現。因此,在目前,無論你對傳統文化是愛是恨,對文化復興運動都可產生力量,最怕的就是對傳統文化毫無感情。有了感情,然後加以理智的開導,卽可有所作為的。
「五四」運動起初純屬一種民主義的政治性的學生運動,但由於民國六年以來的新文學運動做了它的思想背景,因而使其意義加大,內容加深。負起了民國成立以來去除思想上專制的「時代使命」,指引我國走向現代化的道路。其偉大的影響力至今猶存。
民國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國父在致海外同志書中,曾經如此說過:
「自北京大學學生發生五四運動以來,一般愛國靑年,無不以革新思想為將來革新事業的預備。……此種新文化運動,實為最有價值之事。」
現在,政府又把五月四日定為文藝節,來紀念這個偉大的運動。現在算來「五四」運動至今,已整整的五十年了。在五十年後的今天,我們來檢討一下它的得失,是可以作到比較客觀而公正的了。嚴格的說,「五四」絕不是一個文藝復興運動,更談不上文化復興。因為它只有「文」而沒有「藝」。實在只是一個「新文學」的運動而已。這點我們從胡適先生在民國八年十一月出版的「新靑年」雜誌上所寫的那篇「新思潮的意義」中看得很凊楚,他說:
「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種評判的態?……這種評判的態度在實際上表現時,有兩種趨勢。一方面是討論社會上、政治上丶宗敎上、文學上種種間題;一方面是介紹西洋的新思想丶新文學、新信仰。前者是『研究問題』,後者是『輸入學理』,這兩項是新思潮的手段。」
胡適先生沒有注意到藝術,「五四」沒有把藝術列為「研究問題」的對象,也沒有列入「輸入學理」的對象,藝術被「五四」運動所遣忘了。雖然最初的幾年,如同胡適先生所闡述的這種新思潮的特質,曾對孔敎問題、貞操問題丶改良問題、婚姻間题、女子解放問題、父母子女問題丶敎育問題、國語統一問題、文學改良問題、戲劇改良問題、白語文推行的諸多問題上,作過許多研究討論的工作,一時成爲一股汹湧的浪潮。但是,對於介紹西洋新思想的「輸入學理」工作,却顯得雜亂而無系統。就在對西洋新思想一知半解,而對西洋的科學方法尚未學到的時候,「五四」的諸位領導者過早地從事國故整理的工作,以致使得「五四」營養不良,而開不出燦爛的花朶,結不出豐滿的果實,不但淹沒了傳統文化的旣有價値,且妨碍了新文化的發展。
我爲甚麼說它是一個「新文學」的運動,是因為它在白話文學的倡導與創作上,的確有它不可磨滅的功績。這點在此用不着我多說了。當然,在當時受到杜威的實驗哲學與新敎育的理想,以及易卜生的個人主義的強烈影響,其所標榜的「民主、自由、科學」方面,亦有相當的成績,但比起「新文學」來,就相去甚遠了。
「五四」運動忘記了藝術
我之所以說「五四」絕不是一個「文藝復興」的運動,是因為它忘記了「美術」。在此一偉大運動發起的當時,蔡孑民先生曾鄭重地再三呼籲:「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!」 (註一)
他並且指出當時美術界的情形說:
「我們現在除文學界,稍微有點生機外,別的還有什麼?書畫是我們的國粹,都是模仿古人的。」(註二)
蔡元培先生的確是一位有遠見的敎育家,他的倡育並非是見「五四」運動忘記了美術之後才開始的,遠在民國元年二月,在他出任教育總長之後就提出了,在他的「對於敎育方針的意見」中就曾這樣說:
「敎育界所提倡之軍國民主義及實利主義,固為救時之必要,而不可不以公民道德敎育爲中堅。欲養成公民道德,不可不使有一種哲學上之世界觀與人生觀,而涵養此等觀念,不可不注重美育。」
此後,於民國六年,更進一步提出「以美育代宗教說」(註三)
「無論何等宗教,無不有擴張己教,攻擊異敎的條件。宗敎之爲累,一至於此,皆刺激感情之作用爲之也。鑒激刺感情之弊,而專尚陶養感情之術,則莫如舍宗教而易以純粹之美育。純粹之美育,所以陶養吾人之感情。使有高尙純潔之習慣,而使人我之見,利己損人的思念,以漸消沮者也。」
雖然蔡先生不斷的大聲疾呼,呼籲「文化運動不要忘了美育!」結果呢?看請:
「我以前曾經很費了些心血去寫過些文章,提倡人民對美育的注意,當時很多人加以討論,結果無非是紙上空談。」 (註四)
蔡先生儘管一再登高疾呼,盡管他還提出了「美育實施的方法」的具體方案。結果,在意大利文藝復興中坐第一把交椅的美術,畢竟被遺忘了。「五四」運動之不能造成「中國文藝(化)復興」,其最大的原因卽在此。我之所以如此說,並非意味着今日若要談「文藝(化)復興」,就必須把主位讓給藝術家們來坐不可,我只是在建議我們籌劃與推行文化復興運動的諸公,不要再像「五四」那樣,把美術遣忘到一邊去;同時,並提醒我們的藝術家們,不可再逃避責任或看輕自己,我們的地位在文化復興運動中是相當重要的。不要再像「五四」的一代藝術家們那樣,在整個的「五四」運動中交了一張白卷,給民國以來的中國美術史留下一片空白。或許還有人自滿的說:「五四為我們帶來了西洋藝術。」可是,西方藝術的介紹工作實在作得太差,況且還不是「五四」的功勞,因爲沒有「五四」,也會照樣的做到這樣。就如同現在的情形一樣,「中國文化復興運動」未推行之前,已經有許多藝術家在不斷地介紹西洋近代藝術思潮到臺灣來。推行了兩年之後,也未見有任何有系統的介紹工作在作,所作者都是其個別的所好而已。
「五四」時代的畫家們,也許會把責任推諉給動盪不安的社會,說甚麼在這種生活日繁生計日艱的現實環境中,國人所需要的只是物質上的柴米油鹽,不需要藝術。可憐的「藝術家」們,爲了生活,便不得不婢膝奴顏地向惡劣的環境妥協,作些世俗人們所喜愛的東西,不惜將純高的藝術變成討生活的工具。而這些人所能欣賞者,都是那畫得最像的;他們所喜歡的,都是那些他們看得最熟悉的。於是大家一起模仿,模仿那些一般人所喜愛的東西。於是,模仿抄襲之風由此形成,日久之後,就變成一種風氣。俗語說得好,「人必自侮,而後人侮之。」上一代的「大師」們的所作所為,使得社會更加卑視藝術,也越發瞧不起藝術家了。「五四」運動遺棄了藝術,也不能完全怪罪那些領導者沒有眼光,藝術家本身的無志氣,沒抱負也是値得自我反省的。這些自暴自棄的上一代,看在這一代靑年人的眼裡,將怎樣想呢?那麼就再讓我們來看看他們吧。
模仿西洋新的不能代替模仿中國舊有的
民國以來,中國從未有過二十年的安定日子。而在臺灣,我們亨受到二十年的安居樂業,大家都有時間靜下來仔細地想想自己的前途與民族的未來。在我們看到上一代藝術家們的作為悲哀太息與失望之餘,再看看靑年一代,也許會感到些微的安慰。起初的十年間,靑年的藝術工作者們,由於對傳統的中國繪畫失去信心,對自己不甚了解的西洋近代藝術十分嚮往,對歐美當代藝術大師們的旺盛的創造力十分傾倒。於是,大家一窩風地去追求西方的表現材料與工具,模仿西方的技巧與風格。經過一段緊趕直追的迷戀之後,部分的青年畫家由於完全了解了西方近代藝術演變方向之後,迷途知返,浪子囘頭。再用西方現代藝術的眼光來看中國的繪畫傳統,給予它一個新的評價,並欲將傳統中的優點找出來並發揚光大之。換言之,就是試圖將中國優秀的繪畫傳統繼續向前推展,給予它一個新的生命。十年來,「五月畫會」的諸畫家們,即在這一條路埋頭苦幹,深感到我們這一代的藝術家所負的時代使命之重大,毫不猶疑地將這一「文化復興」的重擔放在了自己的肩上。過去的己經過去,時間不留情地把我們拖到了現代的這個漩渦裡。我們用不着膽怯,更不應小看自己,上帝送我們到這個靑黃不接的中國來,必是需要我們,少不了我們,所以總統也經這樣地對我們說:
「靑年是時代的基礎,時代的重心,任何一個時代革新與復興,是無不以靑年的團結與奮鬥,爲其主力,爲其核心的。……」
但是,不幸得很,仍有部分靑年人,由於對上一代保守畫家的不滿,而連帶地對中國繪畫傳統產生了「憎恨」的感倩。還像「五四」時代「打倒孔家店」的啟蒙思想,高唱反傳統。於是,根本不去了解傳統就從心裡排斥傳統,視傳統為毒蛇猛獸。說中國的繪畫早已死亡,應全拋棄。同時又高唱藝術無國界,應創作世界性的現代繪畫。其實,他們所說的「世界性」的「現代」繪畫,就是西洋式的油畫。他們所謂的「現代化」實際上就是「西化」的同意語。所以他們的作品,完全是跟隨著西方的藝術的運動而運動,跟著西洋的畫風轉變而轉變,跟著歐美藝術的思想而思想。歐美有了「普普藝術」(Pop Art),他們就「普普」;有了「歐普藝術」(Op Art),他們又「歐普」起來;有了「硬邊」(Hard Edge),他們立刻又「硬邊」一番。這批青年人對西洋的一切盲目崇拜,甚至對日本的西化程度也非常羨慕、歌頌不已。可是卻不知當一九六六年底,日本的所謂新藝術在紐約近代美術館展出時,紐約時報國際著名的權威藝術批評家肯乃德(John Canaday)在他那篇「新什麼?新在哪裡?」的批評文章中,開章明義地就說:
「上星期,近代美術館擧辦了一個徹底失敗的展覽,叫做新日本繪畫彫刻展」。我覺得它該改名為「舊國際陳腔濫調還魂展」。更為恰當些。他們借屍還魂的工作可做得美極了,既趣味高雅,又技巧無瑕,使得這間美術館的畫廊,在十二月廿六日展覽結束前,看來一時成為市區中裝飾得最精美的一座靈堂,受一具不可見的屍體支配着。」
這就是日本全盤西化的結果。他們比我們西化的年代久,比我們西化的更徹底,他們西化的程度已達到「旣趣味高雅,又技巧無瑕」,遠在我們之上。但到頭來却落得這樣的批評,試想,我們的全盤西化者又將如何呢?藝術永遠不是在一味模仿中可以獲得的。
藝術貴有創造,有創造才有生命才能生生不息。凡真正創造出來的必定是新的,新的就是過去沒有的。可是,一些崇洋的靑年畫家們,將西洋新的畫風模仿了過來,就自認爲「新」了,「現代」了,「創造」了。其實,這種人不是無知,就是自欺欺人。如果我是們僅把眼光局限於臺灣這一地區內,也許是新了,假如我們一旦把眼光放得寬一點,遠一點,那我們就會發現,那旣不新了,也非自己的創造。由此看來,這些年輕藝術家們對上一代如何如何失望,罵他們一代抄襲一代,不知創造爲何物,却很少自我檢討。其實,這兩類畫家只是五十步笑百步,模仿抄則一。所不同者,僅僅是模仿的對象而已。一個是模仿中國古代的大師,一個是模仿西洋的當代流派,全非真正的創造啊!
我早就有感於此,於四五年前就提出了一個口號,那就是:
「模仿新的,不能代替模仿舊的;抄襲西洋的,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。」
中華美術精神是超越的
我從來不反對一個藝術家在學習的過程中,去模仿過去的畫派或畫家,我卻反對把學習的過程當做了目的。世沒有一位偉大演說家生來就會說話的,世上也沒有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不經過一段漫長的模仿路程。模仿是一個過程,也是爲了達到最後個人的創建而必須作的準備。也就因為此,我們可以說,世上所有的反傳統的創造,事實上都是由傳統中走出來,並將傳統延續發展並予以發揚。
還停留在模仿階段的畫家們,竟不了解此,在高唱反傳統之後,而使得他們失去了認識傳統的機會。一些保守的畫家們,見青年學子動不動就打倒學院派的臨摹惡風,反傳統,結果他們「創造」出來的東西又是「亂七八糟」。這兩派的對立,互相攻訐,都是由於思想的偏激,不肯虛心地去認識對方,了解對方。我們這一代的可憐,我們的不進步,就在於對一件事物還沒有認識與了解之前,就妄加批評。中國的傳統中,有壞的,也有好的,有必需拋棄的,也有值得保留的;西洋的傳統中,有好的,亦有壞的,有對我們不適合的,也有我們可以吸收的。總之,一個有思想、有見解、想創造的人,無論對任何一種傳統,都不可能完全接受或完全拒絕。試想,對一件事物沒有十分了解之前,何以決定取捨?所以,在我們接受或反對之前,第一件要做的事,就事先去認識它,了解它。
我認爲,今天的中國藝術家們,如若眞有志於復興中國的藝術文化,僅了解任何一方都不足以擔當起此一重任。我們必須由兩方面去吸取長處,形成一種新風格,才可充分地表現出中華民國這個東西文化交流的時代。我們早已確知, 「文化復興」並非是「文化復古」。任何一個復興的時代,都伴隨著吸收外來文化營養。中國並非是一個保殘守缺的國家,而是一門「寬容大度,兼容並蓄」的民族。所以美國人羅斯(E. A. Ross)在其「變遷中的中國」裡就這樣說過:
「古代中國文化,富於同化力量,景敎入中國,不久消滅,猶太人入開封,失其語言宗敎;或謂中國如大海,凡流入之物,無不溶化,此言誠然。」
向達在其「中外交通小史」中也說:
「中國文化並非孤立,不僅各時代環繞中國的其他各民族想同中國交往,就是自己也不絕地有人抱着玄奘法師『發憤忘食,履險若夷,輕萬死以涉葱河,重一言而之柰苑』的精神,去深入他國。魏晉以後,印度教東來中土,始尙有主客之分,終則成連鷄之勢!」
其次,瑞典漢學家喜龍仁博士(Dr. Osvald Siren)也稱讚「中華的美術精神是超越的」。這些不都證明了中國文化的「寬容大度,兼容並蓄」的美徳與「超越性」的傳統精神嗎?如果國畫家或領導文化復興運動的諸公們,一味劃地爲牢拒絕西洋新思想的影響,就違背了中國文化的傳統精神而無法達到真正的文化復興了。
全盤西化者,只知崇拜西洋現代藝術運動的精神與形式,就說西方的藝術就是世界性的,而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藝術形式就是地域性的。你們當知道當代英國大藝術評論家李德敎授(Prof. Herbert Read)吧!再看看他在其名著「藝術的意義」中如何說的。他說:
「講到中國藝術,吾人不能不想到中國幅員的遼闊廣大,等於英國的極北直至阿拉伯的極南。中國與他國互通聲氣,因而在藝術上互相雷同的地區,當是印度、波斯及日本。如此特質所成立之東方藝術,正如西方峨特式與希臘藝術一樣,乃是超越國境的、世界的。」
我輩靑年人爲何會認爲只有西洋藝術才是世界的,而中國的却不是的呢?
這是懾於西方的物質文明與強大的工業壓力,也是西方經濟文化侵略的結果。年輕人已失去自尊心與自信心,甘願做西方文化的奴隸,做了洋奴還洋洋得意地恥笑別人跟不上時代,沒有現代感。而這種得意洋洋也僅限於在自己的國家裡,在自己的同胞面前。其所以會這樣,是因為他根本就不了解中國文化之偉大,不了解中國藝術的優點與缺點,所以他們竟管整天地喊反傳統,但却說不出個道理來。
聯合國敎育科學文化組織曾經出版過一本書,書名叫作「東方與西方」。作者佛萊廸爾(George Fradier)在書中說過一段這樣的話:
「如果要想勸使歐美人士,試着去認識一個已經除掉了那種富於『畫片性』與『不動性』的年輕而又清醒的東方時,東方人却把一個不甚了解而又不協調的西方,充作一個臨時的東方。」
生在二十世紀的中國,沒有人會說現在的中國不受西洋文明的冲擊,不受西洋新藝術的影響。但是影響不是抄襲,不是全盤接受,不是橫的移植,橫的移植是結不出美好的花果的。屏東的椰子移到臺北來就生不出椰子來;熱帶樹、溫帶樹與寒帶樹在中央山脈上分層生長。任何有生命的東西無不受其環境的影響,何況是一種含有絕大個人主觀意識成分的繪畫呢?我眞寄怪,全盤西化者却對他生活的周圍環境,視若無睹,充耳不聞,硬要說臺北與紐約沒有甚麼差別,這完全是昧着良心說話,在自欺欺人。
創造一個新傳統才是文化復興的目的
我已很不客氣地對保守的與西化的畫家們,做了一次檢討的工作,希望他們不要再各自地鑽著他們的牛角尖,自我陶醉下去。因為這兩種人,對中國的文化復興,都不可能有太大的貢獻。唯有那經過兩種傅統的洗禮之後,站在中國人的立場,站在中國文化的立場,保留中國傳統繪圖中的優點,吸取西洋繪畫的長處,才可能創造出新的、現代的中國作品來。我們生活在中國現代時空的交叉點上,中國現代畫家忽略了縱的時間與橫的空間任何一面的體驗與認知,都是我們的損失,都談不上創造,談不上發揚,更談不上文化復興了。
每個人都很淸楚,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的目的並非復古,它是認識傳統後有選擇地接受傳統,發揚傳統,同時創造一個新傳統。藝術復興的重任,都要靠那些能夠有認識的保留舊經驗,創造新經驗的現代藝術家才能擔負得起來,而這些現代藝術家們還需要社會不斷地給與重視和鼓勵。讓我們大家為迎接這一偉大的文化復興運動而獻出我們的力量來。
註一:見廣益版「蔡孑民先生言行錄」。
註二:同右。
註三:見蔡元培先生在北京神州學會的演講。
註四:見廣益版「蔡孑民先生言行錄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