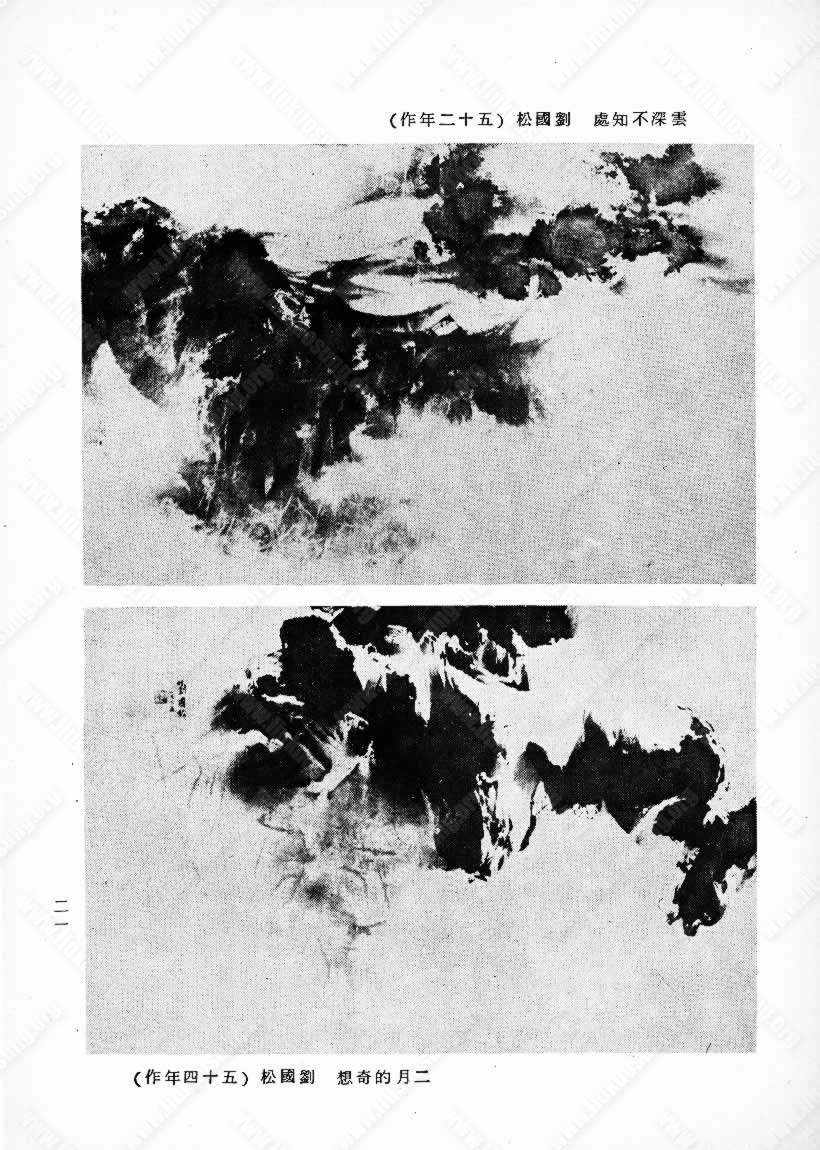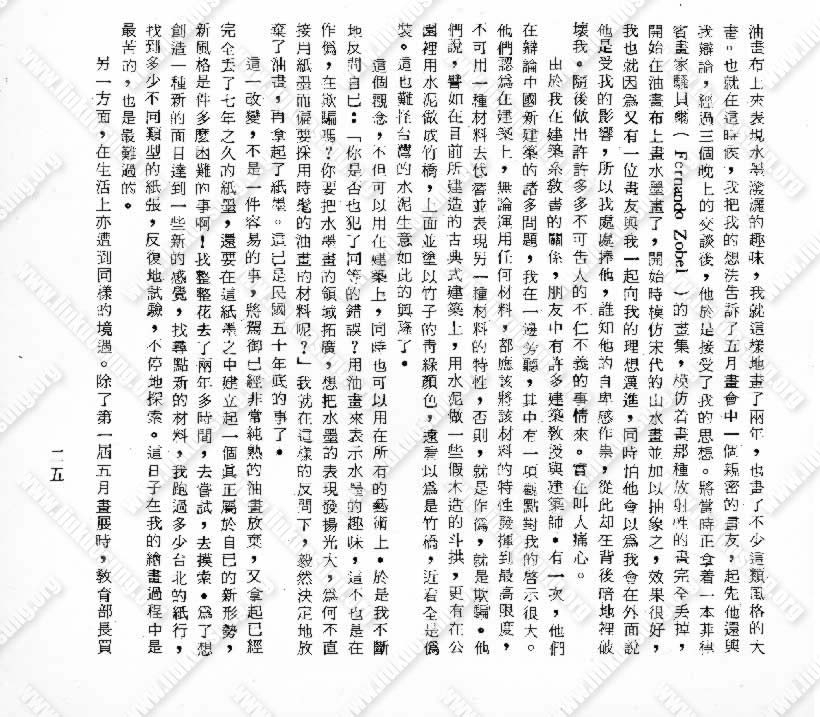繪畫是一條艱苦的歷程
自述與感想
- 期刊與書籍
- 《藝壇》第13期
- 21至29頁
- 1969.4
- 劉國松
法國有本叫做「LEONARDO」的國際性的藝術雜誌,是一九六八年一月創刊的。三個月後,我收到一本創刊號,並且要我寫篇自述性的文章,來談談我自己創造的過程與困難,可是由於我不諳法文,又難找 一位法文好的朋友為我翻譯。雖然後來知道英文也可以,但由於國外安排的個人畫展接連不斷,必需不停地努力作畫,於是一拖到拖今天還未動筆,現在,却經不住「藝壇」發行人姚夢谷先生的催促,只得暫停下畫筆來,說說我從事繪畫的經過與感想了。
繪畫是一個非常艱苦的歷程,那是需要不斷努力。堅強的毅力,超群的思想,遠大的眼光,偉大的抱負以及過人的才智。任何一個成功的藝術家,沒有不具備這些條件的。因此,自從我十四歲開始正式畫畫以來,越畫越覺得困難,越畫越覺得這條路的艱苦。
過去,我總覺得明清以來抄襲摸仿之風太盛,沒有出過多少有創造性的畫家,又怪當今做父母的不鼓勵自己的子女從事藝術工作。以致藝術水準低落。可是現在呢?我的想法卻多少有些改變。當我在歐遊歸國之後,我發誓不再勸靑年入從事藝術工作。因為我明白了。一個眞正熱愛藝術,才智過人的青年,你不鼓勵他,甚至還阻止他從事藝術工作,他仍然會堅持走上這條路的。他對自己具有無比的信心,也必忠於他所從事的工作。否則,就是受人鼓勵勉強走上去,也只好東抄抄克蘭因,西抄抄蓋俄(Winfred Gaul),對社會又有何益呢?
我自小就不是一個富有的孩子,當我六歲的時候,父母就爲了抵抗日本人的侵略戰死在沙場,母親帶著我兄妺二人過著流浪的生活。我上山砍過柴,母親做過工,吃過鹽水泡發了霉結成塊的米飯,凍著睡不着母子三人抱着默默流淚。也許就是這種生活把我鍛鍊成一個不怕困苦的堅強個性;也許就因爲這樣,讓我覺得世上沒有甚麼可怕而大不了的事情。任何外來的打擊,對我來說,都是不足輕重的。我堅信一個原則: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。只有眞正的學術才是永遠不能被打倒或抹煞的。
我由小學開始就熱愛兩門功課。一是圖畫,一是國文,我喜歡畫畫,同時也愛看書,記得在四年級時畫的畫就被老師拿到五六年級的班上去給他們看。五年級時我的一篇「流亡五年」在湖南祁陽梧溪日報上刊出之後,贏得了不少人的眼淚與同情的信函。這兩條平行的志趣一直維持到我進入師大藝術系才有所消長。在這之前上,我是以真名與魯亭、爾眉、意清的筆名發表我的文章,我發表過的第一首新詩,是高中一年級時寫的「哥兒們」,在自由中國雜誌上刊出。中學生雜誌上也常有我的散文。到高二下學期期考前不久,我才決定專攻繪畫的,於是高三沒讀就以同等學歷考進了師大藝術系,正式開始了藝術的旅程。在二年級以前還念念不忘地寫新詩,與當時旁系同學陳慧與童山合編了一份「細流」詩刊,那時台大的詩人余光中的「藍色的羽毛」還未出版。現在說來已是很遠很遠的了,恐怕很少有人知道我曾經也想做個所謂的「新詩人」吧。後來,我專心一意地畫畫之後,雖然也常常讀讀別人的詩,但由於自己不再寫作,所以有友人談論新詩時,我從來也不插嘴以表示自己很懂,就是有入問起我時,我也從不對任何新詩人妄加批評。我之所以這樣作,一來我了解創作者的辛苦,不能用一句話就把人家的辛苦給否定了;二來我不斷地提醒自己,不太了解的事情不要信口雌黃,以作到作者的尊重與對藝術的「誠」。可是相反地,我却看到一些所謂的「現代詩人」,對自己並不甚了解的繪畫,却侈談高下優劣,胡捧亂罵,以造成文藝界的惡勢力,實在使人啼笑皆非。
勝利的第二年,我十四歲,讀初中二年級,那時每天上學時都經過兩家裱畫店。放學時,我總是在這兩家裱畫店花去很多時間,看那牆上經常更換的畫。日子久了,其中一家的老板就開始找我說話,問這問那的,後來知道我家境貧窮,喜畫而無力學,於是他就給了我大批的零碎紙張及舊筆,我畫了就拿給他看,他給予我不少指點,也不斷地供我紙張筆墨。我記得二年級那個暑假,我就像發了狂似的每天畫,有時那老板認爲我畫的較好者,他就留下了,也有時拿給他的畫家主顧們看。就因爲此,後來我到了南京國民革命軍遺族學校謮三下時,就開始 被師長們稱作小畫家了,我的許多畫都被學校拿去裱好,掛在校長 蔣公與主席校董蔣夫人的休息室裡,其他如貴賓室,會客室中也都掛的有。
到了藝術系二年級後的暑假,我開始對西洋繪畫發生了濃厚的興趣,同時覺得中國繪畫巳缺乏活力,要想使其恢復活力,必須注入新的養份或新的血液,於是我開始讀些美術史與藝術理論的書籍,同時開始全心全意地從事西洋繪畫的硏究。由於我每年只靠極少的撫卹金來買顏料用具,我又不願把時間浪費在家敎或替人作廣吿上,所以畫不起油畫,(油畫箱都是朱德群老師送我的),只有畫水彩。也就因為此,在畢業之前的畫展中,獲得了水彩畫的第一獎,同時又得到國畫的第三,最後並以笫一名由師範大學藝術系畢業。那時,我除了沒有時間也沒有那種習慣往敎授家跑和不懂奉承人之外,我可稱得上是一個好學生了。只有少數幾位老師在背後說我有些驕傲而巳。
當我生平第一次一下子領到兩個月薪水時,我幾乎全部買了油畫顏料,從此又放下了水彩猛畫油畫了。
畢業後的第二年,與同班的其他三位同學,在母校的敎室裡舉行過一次四人聯合畫展,隨後即是「五月畫會」的創立,那是民國四十五年的事。四十六年五月展出第一屆,至今已有十三年的歴史了。
那時我們成立五月畫會有幾個理由與目的的。其中最主要的一點,是因見當時藝術界的死氣沉沉,毫無生氣可言,而我們又是剛剛由學校畢業,生氣勃勃,充滿理想,那裡忍受得了那種凝滯的氣氛,於是想藉我們率直而銳利的「感受性」 和大膽而潑辣的「表現力」,以及蓬蓬勃勃的活力與朝氣,來剌激一下那消沉的藝壇,稍事振作,使封凍已久的創造力起死回生。這點,我們已達到了某種程度的帶頭作用,東方畫會、現代版畫會等的相繼成立,在近十年來的中國藝壇,掀起了一次對西洋近代繪畫研究的高潮。因而也引進了一些新的觀念,新的理論,新的技巧以及新的營養。同時也使得見識不廣的靑年學子,誤把這種學習的過程,當作了創作,當作了目的,以至緊追西洋流行的畫派不捨,進而不能自拔,自認是有「現代感」的現代人,他們所畫的才是「現代畫」呢。這種錯誤觀念的造成,我們也不能不負一些責任的。因爲最初,我們就是以模仿西洋近代畫派如野獸派、表現派、立體派、超現實派等等開始的。那時由於我們見識的不廣,學識的淺薄,總以爲模仿了一種西洋旣有的,而國內還無人嚐試過的所謂的「新」風格,就自認爲自己思想比別人新,比別人具有現代感,目空一切,罵傳統的中國畫家不求長進,不知創造爲何物。這樣在無知與淺薄中我們過了五年,到了四十八年第三屆五月畫展之後,我才開始覺悟到這樣一味地模仿西洋新運動,新派別,並不是一條正確的道路,於是我反省再反省,考慮再考慮,那正是我離開了台北的熱鬧圈子而南下到成功大學作助教的時侯,那裡的寧靜與孤獨,給了我一個沉思靜想的大好機會,我漸漸覺得民族風格的重要,任何一位有創造性的畫家都離不開他自己的傳統,也無需特別排斥。這是我繪畫思想的轉戾點,也是浪子回頭的一年。
那時,我確信民族性的表現在於精神,而不在於材料工具,在表覡風格上,我欲將停滯不前的中國傳統繪畫向前推展並發揚光大。所以我利用西洋繪畫的材料在油畫布上來表現水墨潑灑的趣味,我就這樣地畫了兩年,也畫了不少這類風格的大畫。也就在這時候,我把我的想法吿訴了五月畫會中一個親密的畫友,起先他還與我辯論,經過三個晚上的交談後,他於是接受了的思想。將當時正拿著一本菲律賓畫家騷貝爾(Fernando Zobel) 的畫集,模仿着畫那種放射性的畫完全丟掉,開始在油布上畫水墨畫了,開始時模仿宋代的山水畫並加以抽象之,效果很好,我也就因為又有一位畫友與我一起向我的理想邁進,同時怕他會以爲我外面說他是受我的影響,所以我處處捧他,誰知他的自卑感作祟,從此卻在背後暗地裡坡壞我。隨後做出許許多多不可吿人的不仁不義的事情來。實在叫人痛心
由於我在建築系敎書的關係,朋友中有許多建築敎授與建築師,有一次,他們在討論中國新建築的諸多問題,我在一邊旁聽,其中有一項觀點對我的啟示很大。他們認爲在建築上,無論運用任何材料,都應該將該材料的特性發揮到最高限度,不可用一種材料去代替並表現另一種材料的特栍,否則,就是作偽,就是欺騙,他們說,譬如在目前所建造的古典式建築上,用水泥做一些假木造斗拱,更有在公園裡用水泥做成竹橋,上面並塗以竹子的靑綠顏色,遠看還爲是竹橋,近看全是偽裝。這也難怪台灣的水泥生意如此的興隆了。
這個觀念,不但可以用在建築上,同時也可以用在所有的藝術上,於是我不斷地反問自已:「你是否也犯了同等的錯誤?用油畫來表示水墨的趣味,這不也是在作僞,在欺騙嗎?你要把水墨畫的領域拓廣,想把水墨的表現發揚光大,爲何不直接用紙墨而偏要採用時髦的油畫材料呢?」我就在這檨的反問下,毅然決定地放棄了油畫,再拿起了紙墨。這已是民國五十年底的事了。
這一改變,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將駕御已經非常純熟的油畫放棄,又拿起已經完全丢了七年之久的紙墨,還要在這紙墨之中建立起一個眞正屬於自已的新形勢,新風格是件多麽困難的事啊!我整整花去了兩年多時間,去嘗試,去摸索,為了想創造一種新的面目達到一些新的感覺,找尋點新的材料,我跑過多少台北的紙行,找到多少不同類型的紙張,反復地試驗,不停地探索。這日子在我的繪畫過程中是最苦的,也是最難過的。
另一方面,在生活上亦遭到同樣的境遇。除了第一屆五月畫展時,教育部長買過我一張畫以示鼓勵之外,一直展出到第七屆時沒賣過一幅畫,但每年花在畫上的錢却不在少數。五十年結婚後,妻與我兩人的收入不夠生活之需,但妻絕不肯讓我去向朋友或學校借貸。他說我們不能靠借貸過日子的。於是她自動出差(過去不願去的地方也自動去了),節省下來的出差費,補貼家用。而我呢?却靠賺些稿費來養畫。第一個小孩誕生之後,這種情形就更加嚴重了,我們生活再苦却從來向任何哭過窮,朋友們來時仍然盡我們的能力招待他們。那時妻也會勸我收幾個學生,但我却寧可多看點書賺點稿費,而不願把時間浪費在小孩子身上。更使我安慰的是,妻從未要求過我去畫點廣吿或討人喜歡而又容易賣的畫,否則,我會吿訴她,我絕對不賤賣我的藝術生命,更不侮辱藝術的尊嚴。一個真正忠於藝術的畫家,在同一個時期是絕不畫第二種不同風格的畫的,他在藝術研究的過程中,不同時期有不同的思想,但不會在同一時期有多種不同的繪畫思想。否則,他就是根本沒有思想(沒有一種思想是屬於他自已的)。對藝術不諴,繪畫謹是他爲了達到利與名的工具和手段而已。
嚴格地說起來,我雖然從十四歲開始畫國畫,十九歲進入師大藝衛系,但眞正藝術生命的開始,還是民國五十二年我三十一歲的時侯。那年我才眞正地找到了我自已逐漸地形成了我自已的風格,自已的面貌。經過了那段臨產前的痛苦之後,我獲得藝術的新生命,當時眼看着逐漸顯現的新風格,那喜侻是難以形容的,只有有過這種經驗或抱着剛出世的兒子的母親才能體得出吧。
接著,五十三年在省立博物館所舉行的第八屆五月畫展的第一天,我開始賣出了第一幅畫了,沒想到畫展結束時竟賣出三幅之多,賣畫並非是畫家的目的,但是沒有一個畫家不希望他的作品被人欣賞,被人讚美的。如何才能證明人家的讚美是發自內心,欣賞是出於眞實的呢?那就是一個陌生人肯拿出錢來收購你的作品。因此,當那立哥倫比亞大學的敎授第一個對我說他要買我的一幅畫時,我真感動得幾乎流出眼淚來,我眞想把那畫送給這第一位的知音。因爲他所欣賞的,並不是其他大畫家們的影子,而眞正自已所創作出的新繪畫。我之所以稱其爲「新 繪畫」,不僅是說明過去沒有畫家畫過我這樣的畫,而且在過去的類型中還找不到一個適當的位置來歸納我的畫。因此,國畫家說我的畫是西洋畫,西洋畫家却又說我的畫是中國畫。其實這也正是我所追求的,我要在二者之間走出一條新路來,它旣是中國的,又是現代的。我爲了倡導這種「中國現代畫」的理想與主張,曾經在那時提出過一個口號,那就是:
「模仿新的,不能代替模仿舊的;
抄襲西洋的,不能代替抄襲中國的。」
五十二年的春天,經名詩人余光中敎授的介紹,得認識了由愛荷華大學來的李鑄晉敎授,在他臨去日本三個小時之前來我畫室看五月畫會的畫,當時看了我的畫之後即對我說:「我腦子中所想像中國繪畫所應發展的路子,你已經全表現出來了。我來時,曾想如果中國當代有些優秀的畫家時,我將爲這些畫家在美國安排一個巡迴聯展,可是在我到了香港與台灣之後,始終沒有決定此一計劃,今天看到你們畫之後,我回去之後決定安排這項展覽了。」這就是後來在美國巡迴展覽兩年的「中國新山水傳統」畫展。
由於李鑄晉敎授的推荐,洛克裴勒三世基全會的主任特別到台灣來了一趟,親自看了我的畫,對我的畫又特別喜歡,於是他第一個給了我槳全,讓我有一個做夢都不敢想的機會作一次環球旅行參觀,到美後,又因我的表現良好,作品到處受到藝術界的好評,基金會又將我一年的的獎金延長爲兩年。在那兩年中,共訪問了十八個國家外加西柏林及香港,參觀了將近一百個美術館與博物館。可說是應該看的都看到了。不但增廣不少見識,而且對自已的創作與理想,更增加了很大的信心。因爲它已經接受過世界藝壇嚴格的考驗了。
在過去的三年中,我在國外已經應邀舉行過十七次個人畫展,其中有七次是在美術館與博物館中展出,並已有九個博物館中收藏了我的作品,最多者如舊金山世界第一流的德揚博物館,已經先後收藏了我六件不同時期的作品。各處對我的畫展給予極好批評的報紙及雜誌(包括紐約時報及藝術雜誌,藝術新聞雜誌在內)共二十六篇。並且還與目前紐約最大的現代畫畫廊簽有長期合約,這也是所有的當代畫家所夢寐以求的,可是在所有由台灣出去過或仍留國外的畫家中,我是唯一簽有這種合約的。並且我還在美國第一屆「主流」國際美展中獲得「傑出畫家奬」的榮譽。可是嫉妬我的人,爲了掩飾自已在外失意的事實,把我的這些他夢寐以求不到的榮譽一皆抹煞,却儘量宣傳我的賣畫,進而再說賣畫與純藝術無關。不錯,自從我賣第一幅畫到現在,我已賣出了兩百多幅了,最高的價錢已賣到三千美金,那是德揚博物館買去的,一個博物館是那麼輕易地就拿出那麼多錢來買一幅沒有價値的畫嗎?你好,為甚麼拿著爸爸的介紹信到處去見博物館館長,而都不能買你一幅呢?利用關係在美國一個小城開展覽,却以薄利多銷的生意手法來賤賣他那種爲了引起外國人暫時好奇的,在畫上寫着中國字的假中國畫以圖利。自己不努力,一味耍手段,走捷徑,借攻訐別人以抬高自己,那是永遠也走不進藝術的正途的。
所遺憾的,有些年青人,自已不知埋頭苦幹,一心投機取巧。如果見到別人由於努力而有所收獲時,就想盡方法破壞之,不允許別人出頭,近年來,政府與民間團體設立了許多獎勵辦法,爲的就是提掖人才,讓有才智及肯努力的靑年出頭。說實在的,培植一個人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我們在國際藝壇上就只有一個趙無極,而且還是法國人培植出來的,我們感到高興驕傲都嫌太遲了,何致於還要去攻擊他,謾駡他呢?不要把眼睛老盯着別人,多看看自已,多作些反省的工夫,是對自己有益,也是對社會有妤處的。
正值政府與全國上下推行文化復興運動的今日,一些曾一味高唱全盤西化者,現在也知民族性的重要,轉轅易轍了,既然我們大家的目標是一個,方向已一致,我們就應該共同努力,向前邁進,以期早日實現我們文化復興的理想。